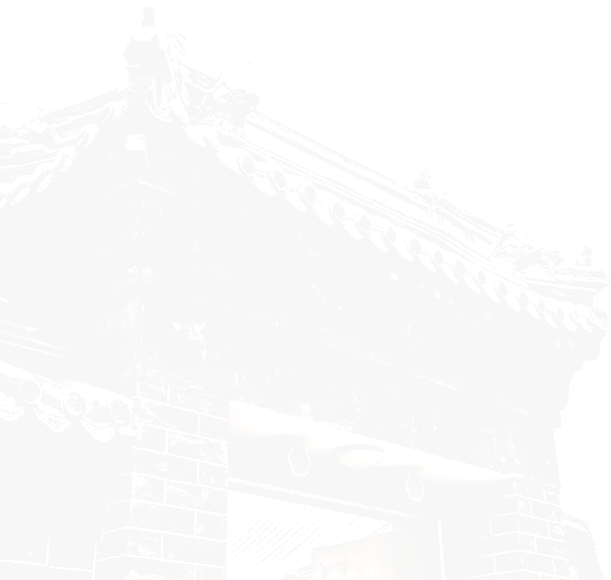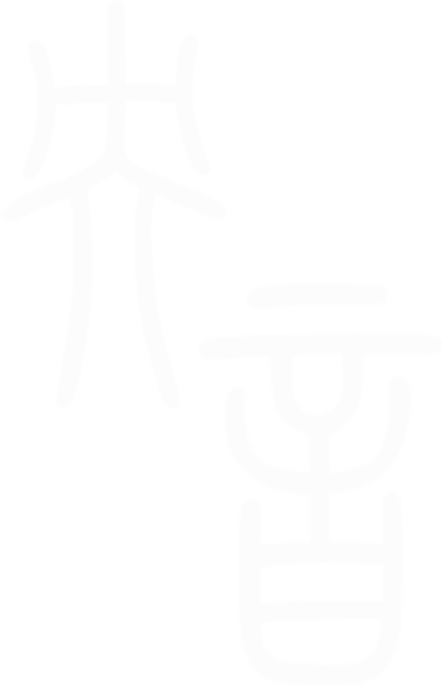黄晓和简历:
音乐学家,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西方音乐史教授、博士生导师。1935年1月生于江苏镇江,祖籍贵州贵阳。1946年考入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学习小提琴。1949年10月进入北京人民文工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前身)任独奏员和乐队队员。1950年5月进入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少年班。1954年公派赴苏联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先后师从大卫·奥伊斯特拉赫教授主修小提琴、师从谢尔盖·斯克列勃科夫教授主修音乐作品分析。1961年毕业,获“音乐学家、理论家”资格,并回母校任教。曾开设“曲式与作品分析”“外国音乐名作”“西方音乐通史”“苏联音乐史”“苏联音乐名作”和“音乐学分析”(合作)等课程,出版《西方音乐通史》(合作)《外国音乐简史》《西方音乐史与名作赏析》《苏联音乐史》上卷(1917—1953)》《心灵的回响——世界交响乐名曲赏析》和《西方歌剧解析——构成·种类·流派·历史·名作》(合作)《现代音乐欣赏辞典》(合作)等著作,发表《俄罗斯英烈的心声——评介苏联歌剧<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旧制度灭亡的丧钟 新世纪诞生的凯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歌曲评介》《< 伊多美涅奥>——莫扎特歌剧创作原则的初步体现》《时代·生活·思想·创作——纪念柴科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上下篇)《肖斯塔科维奇——特殊时代锤炼的作曲大师》《关于“无标题音乐”大批判的前前后后》和《实现了“交响梦”的作曲大师——朱践耳》等论文及数十篇有关中外音乐的乐评文章。
我于1935年1月出生在江苏镇江,祖籍贵州贵阳。我的家庭有两个特点,一是推崇民主进步思想,家族中有3人成为革命烈士。我的祖父黄干夫是贵州新学教育的先行者、贵阳达德学堂创始人,叔祖父黄齐生是爱国民主人士和著名教育家,表伯王若飞是我党早期的杰出革命家,2009年被中宣部、中组部等部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二是爱好棋琴书画,书香气息浓郁。我的爷爷擅长绘画,会弹古琴。我的父亲从事美术工作,喜欢听外国音乐唱片,并会演奏小提琴、扬琴、锯琴等乐器。在这样的家庭中,我深受进步思想影响,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音乐道路。
踏入校门:大哥形象,人生榜样
我们家6个兄弟姐妹全都投身于音乐事业①,其中更有4人曾在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含其前身单位)学习和工作。特别是我的大哥黄晓庄,曾在重庆国立音乐院短期学习钢琴,后又进入育才学校学习大提琴,并创作了不少音乐作品。抗战时期,他和我的叔祖父黄齐生一起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大提琴并担任音乐教员。1946年4月8日,在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英年早逝(史称“四八”烈士,其中有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重要人物)。我非常敬佩我的大哥,也很希望能够以大哥为榜样成为一名革命音乐家。
左图:在“四八”空难事件中牺牲的大哥黄晓庄
右图:延安革命纪念馆对“四八”烈士的介绍
20世纪50年代,黄晓和与二哥黄晓同、大姐黄晓芬、二姐黄晓苏、小妹黄晓芝合影(按前后顺序)
1946年春,我在上海的报纸上看到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的招生广告,因为喜欢音乐,又因是免费就读,能够给家庭减轻经济负担,便在二姐的带领下前去报考。经过文化基础测试和对音高、旋律、节拍、节奏的基本感知能力的考察,我被录取,并于当年深秋赴常州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报到。幼年班的学生(年龄从11岁到16岁不等)大多出身于贫苦家庭,平日接触音乐的机会较少,尤其是西洋音乐。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吴伯超院长专门请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外籍犹太音乐家,在灵官庙(幼年班在常州校址)的礼堂里举办音乐会。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场三重奏音乐会,那是我第一次听音乐会,西方古典音乐独特的艺术魅力,令我陶醉,久久不能忘怀,也使我对未来的音乐学习之路充满向往与憧憬。
入学之后,学校根据我的条件,让我跟随盛天洞(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盛雪)老师学习小提琴。盛老师的教学以认真、严谨而著称,尤其对演奏姿势和音准等问题要求严格。在他的指导下我进步很快,第二年就在南京首次登台独奏维瓦尔第《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国立音乐院乐队伴奏)。除主科外,幼年班还开设其它一些音乐课(视唱练耳、音乐欣赏等)和文化课,为我们打下了较为扎实、全面的音乐基础。
1947年,在南京国立音乐院礼堂排练维瓦尔第《a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照片由美国新闻处记者拍摄
1948年秋到1949年春,战乱升级,社会动荡不断加剧,物价飞涨,幼年班在办学经费上遇到很大困难,只得让一部分有家的学生暂离学校。我回到上海家里,继续坚持学琴练琴,并在王人艺先生的指导和推荐下,参加了由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举办的“第一次儿童音乐比赛会”(1949年4月),获得乐队乐器组小提琴头等奖。幼年班还有多名同学也参加了这项比赛,基本包揽了乐队乐器组全部奖项,其中大提琴头等奖是盛明耀、二等奖马育弟,小提琴二等奖高经华,长笛二等奖沈兴华。另有刘诗昆获钢琴组头等奖,方国庆获该组二等奖。
上图:1949年4月摄于上海
下图:在上海“第一次儿童音乐比赛会”中获得乐队乐器组小提琴一等奖。领奖照片中有比赛发起和赞助者戴天吉夫人和小提琴教师张隽伟
1949年秋,追随大哥投身革命文艺工作的大姐黄晓芬,作为“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团员,赴匈牙利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回国后又与苏联派来的第一个文化代表团一起,到上海等城市演出。当时我正在育才学校音乐组学习,大姐给了我一个“大显身手”的表演机会。当我为她的同事们演奏完几首小提琴曲后,金紫光团长当即决定吸收我加入北京人民文工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前身),于是我就随该团一起到了北京,成为小提琴独奏员和乐队队员。当年冬季的一天,我在中南海为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表演了小提琴独奏。当大姐领我到毛主席身边时,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贵州贵阳人。毛主席立刻伸出三个指头说:“过三天贵阳就解放”。我瞬间高兴得跳了起来!此后的每天我都去收发室看报纸,终于在第四天(1949年11月15日)看到了《人民日报》上刊登的“贵阳解放”四个大字,顿时心潮澎湃,伟人的音容笑貌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1950年,北京人民文工团管弦乐队
上图:排练柴科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独奏黎国荃,指挥李德伦,乐队最左边为黄晓和
下图:乐队成员集体听唱片,最外圈中坐者为黄晓和
1950年春,南京国立音乐院及常州幼年班的全体师生北上天津,与新成立的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实现“大团圆”,我也重新“归队”返回校园,成为“央音”少年班的一员。少年班的学习生活丰富多彩,学校经常组织我们深入工厂、农村、部队,为基层群众举办各种音乐会、讲座和开展歌咏活动,也常有外国艺术家代表团来校访问交流,令我们的艺术视野大为开阔。在幼年班,我除了先后跟随褚耀武和马思聪先生继续学习小提琴外,还学习了中国民族乐器板胡。这得益于吕骥同志(时任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对民族音乐教育的重视。他要求每个学生在本专业外必须学一件民族乐器。
那时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1951年夏天我光荣入选中国少年先锋队出国代表队,参加了在民主德国举办的国际少先队夏令营活动。当时我国一共组建了三个代表队,另外两个代表队分别被派往苏联和保加利亚。我所在的代表队由11名学生组成,我任副队长兼队旗手。到了民主德国后,我又被选为夏令营开幕式的升旗手,与民主德国和来自波兰的少先队员一同升旗。活动期间,我们为当地观众表演了精彩的音乐舞蹈节目,展现了新中国少先队员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在民主德国参加国际少先队夏令营活动
上图,“少四班”小提琴专业同学合影,前排左起:张志勤、闵乃权、刘天明
后排左起:林耀基、岑元鼎、黄晓和、李向阳、杨大风
下图:1950年暑假,参加由学校组织的暑期演出队,赴济南、开封、西安等地巡演,前排右1蹲者黄晓和,其身后站立者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
留学苏联:选定专业,奋发图强
受家庭影响,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有了去苏联留学的愿望。1953年,也就是在我来到少年班学习的第三年,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经过专业主科以及政治、文化课的考试,我获得公派去苏联留学的资格,并在7个月的俄语强化训练后,于次年赴莫斯科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
我们是国家派往苏联的第二批音乐专业留学生,受到了苏联方面的高度重视。斯维什尼科夫院长亲自接见我们,并一一征询每个人的学习愿望。我随即表达了想跟苏联著名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学习的意愿。虽然奥伊斯特拉赫的工作十分繁忙,学生很多,但院长还是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使我成为“老奥”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学生。可是,在学习小提琴的两年半时间里,因为“老奥”国内外演出活动太忙,我只跟他上过两次课,其余时间则由他的助教邦达连科副教授上课——这并不是特例,“老奥”所有的学生大多数时间都是由助教代课,只有准备参加国际比赛的特别优秀的学生,才能够比较多地获得“老奥”的指导。
有幸成为中国派到苏联的第一个小提琴专业留学生
虽然我的小提琴演奏水平当时在国内算是拔尖的,但与苏联同学相比,差距还是非常悬殊。于是,我倍加用功地练琴,甚至在因不适应莫斯科的寒冷气候而经常感冒时,也继续坚持练琴。最终,却因过度劳累,导致左臂经脉肌肉劳损。在努力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治疗之后,左臂仍然十分疼痛,连稳定持琴都无法做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下决心转专业。经多方考虑并通过考核,我从管弦系转入理论作曲系,师从谢尔盖·斯克列勃科夫教授主修音乐作品分析专业。
留苏生活丰富多彩
右上图:1958年在莫斯科远郊集体农庄与同学们的合影。前排三名中国留学生,右起:黄晓和、曹鹏、朱践耳
右下图:1955年五一劳动节,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门前与同学们合影
转入理论作曲系后,我从二年级开始上课,但同时还需补修一年级的所有课程。“柴院”音乐演奏小厅顶层有一个专门的录音室,里面收藏了大量的音乐唱片和磁带。我因为音乐基础薄弱,所以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那个狭小而寒冷的录音室外的过道里,带上耳机听大量音乐作品。理论作曲系的政治课有“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美学基础”等,专业课主要有“外国音乐史与音乐名作”“俄罗斯音乐史与音乐名作”“苏联音乐史与音乐名作”“苏联各民族音乐史与音乐名作”“俄罗斯民歌”“和声学”“音乐作品分析”“复调”“配器与总谱分析”“总谱读法”和“钢琴”等。我在理论作曲系一共学习了4年半,顺利修毕了所有课程,成绩优秀。同时,我还按照学校要求,参与了多种多样的实习活动(如去附中教课,担任校外音乐会的解说等)。我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在苏联的首次演出,节目单解说就是我写的。
1957年,毛主席在我国驻苏使馆,与使馆工作人员和部分留苏学生交谈,站立第一排左3为黄晓和
1961年5月我参加了苏联的“国家考试”,其中包括当场分析一部作品和即兴键盘和声测试,最后是毕业论文《论简单一部曲式》概述与答辩。在“柴院”颁发我的毕业证书上,注明我获得“音乐学家、理论家”资格。当年7月我回到母校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从事教学工作。
1961年5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论文答辩会上
回国任教:发挥专长,报效祖国
我回国后,起先在作曲系任教。在担任一段时间吴祖强教授的助教后,开始独立讲授《曲式与作品分析》课程,并编写了上中下3册油印本教材。这些教材由当时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江文也先生帮我刻写。他能助我一臂之力,我非常感激。
1973年,按照当时的中央“文化组”的指示,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组织成立了一个编写组,以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教师为骨干力量,吸收全国各地音乐学院的部分教师和研究人员,撰写《西方音乐史》。编写组由李佺民任组长,我和汪毓和任副组长。因受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左思潮影响,史稿的编写缺乏事实求是的态度,事后被大家彻底否定。
《西方音乐史》编写组成员合影,第三排左4为黄晓和
正是由于这一经历,“文革”结束后,我便留在了音乐学系,从事外国音乐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改革开放后,随着学术研究思想的解放和外国音乐资料的增加,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条件愈发成熟。我起初主要从事西方古典音乐研究,1984年以后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所缓和,于是我决定将研究重心转向苏联音乐。我认为苏联音乐的成功经验和经历的挫折,对于中国而言,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地去看待和理解它。如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哈恰图良、卡巴列夫斯基等作曲家的作品,曾一度被批判为形式主义,但实际上他们的创作是当代音乐的宝贵精神财富。20世纪是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文化思想激烈动荡的年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音乐的表达需要一些突破来适应更为复杂的思想内容,例如对调性关系的扩充与创新,就是突出的贡献。我认为,在音乐创作中,没有不好的技术,只有不好的运用。一个优秀的作曲家需要将技术手法和音乐表现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技术上有所突破的同时使艺术表现力更加丰富,更能够深刻反映时代精神。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将相关研究成果反哺于教学,开设了“苏联音乐史”选修课。没想到当时选课的同学非常多,远远超过教室容量,而不得不分为两个班进行授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黄晓和教授将研究重心转向苏联音乐
黄晓和教授出版的部分学术著述
另外,虽然主要从事外国音乐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我始终认为研究外国音乐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和发展中国现代音乐,因此我也一直十分重视和关心中国音乐的发展,曾发表多篇有关朱践耳、王西麟、金湘、马思聪,谭盾、郭文景等人音乐创作的文章。
与作曲家朱践耳合影(摄于20世纪90年代初)
从1987年开始,我相继担任音乐学系副系主任和系主任。在此期间,该系在外国音乐领域除了深入研究西方古典音乐以外,特别加强了对西方现代音乐和苏联音乐的研究,此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领域,即亚非拉音乐研究(现为世界民族音乐研究),使外国音乐研究领域得到明显的扩大和丰富。
黄晓和教授在为学生上课(摄于20世纪90年代初)
除了上专业大课,我还曾指导西方音乐史专业博士生5名,硕士生14名,本科生9名。在教学中,我特别强调音乐学系学生要重视作曲技术理论“四大件”(和声、复调、曲式、配器)的学习。我们有很多学生不重视“四大件”,在写论文时忽略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没有深入到音乐当中去。相反,却大量论述音乐之外的内容,这是不可取的。无论怎样定义音乐学这门学科,它归根到底离不开音乐本身,离开了音乐,就不成为音乐学了。因此,我觉得,音乐本体研究应该始终是音乐学研究核心中的核心。音乐学系的学生应该加强对作曲技术理论“四大件”的学习,而在掌握音乐本体分析技能的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到社会音乐生活中去,放下所谓“专业”的架子,像普通听众一样去欣赏音乐,整体性地感受音乐,理解音乐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我认为,一个合格的音乐学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热爱音乐、对音乐十分敏感的人,同时还应具备必要的音乐理论(包括作曲技术理论)知识、音乐实践能力和历史人文修养。从事音乐研究,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够算真正地掌握学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会
上图:学生刘红柱与导师黄晓和
下图:左起周耀群、俞人豪、钟子林教授,学生李秀军,导师黄晓和,李应华、蔡良玉、王惜扬教授
中国的音乐理论工作者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思想的基础上,不断开阔眼界、开拓思路,以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借鉴、吸收其他一切科学的、合理的研究方法。如今,我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依然十分关心社会音乐生活,也一直坚持笔耕不辍。多听、多看、多思考、多总结,这是音乐理论工作者的基本功,希望能够与年轻的老师和同学们共勉。
注:
①大哥黄晓庄学作曲,大姐黄晓芬学大提琴,二姐黄晓苏学声乐,二哥黄晓同学指挥,小妹黄晓芝学小提琴。
供稿:档案馆(校史馆)
采访:宋学军、张乐、李欣阳
撰写:宋学军、李欣阳
校对、设计:李梅
编辑:刘露蓉
本文为原创内容(图片由黄晓和教授提供),未经同意禁止商用、转载。文章及图片版权归香港内部正版资料大全档案馆(校史馆)所有。